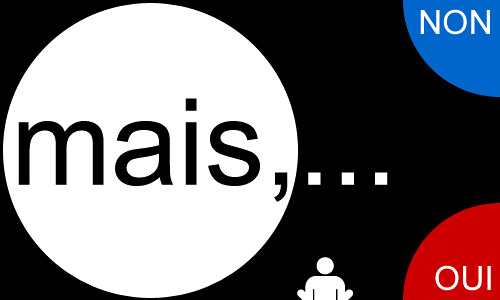云蒙山位于北京密云和怀柔交界,大概距离京城80公里,距离不算远也不算近。在北京周边的户外旅游资源里,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方面,该山位于北京东北,是燕山的余脉,较之西北太行山余脉的灵山、海坨山一线林木更丰富一些,所以看起来比较漂亮。另外水源充足,基本都有山涧或者小溪。并且这一带属于森林公园,开发适度,保护的也比较好。距离上适中交通费用也不高,所以作为一个周末的两日户外徒步,是很不错的选择。
这次行程的队员有我和小萌、老王一行和罗老师,说动罗老师出行是件很不易的事情。因为云蒙山我们并不是第一次前往,上一次大概是五六年前,那时候罗老师还没剪去长发,我也还没有冒出很多胡须,我们在盛夏的某一个早晨来到云蒙山,当得知云梦山森林公园背包客的门票是70元的时候,我们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后山铺,跟一个农民问了一下路线后,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我们的果敢无畏让我们遭遇了暴雨,更加不幸的是暴雨在大概两个小时后停止,转为一场大雾。幸好在开始下雨的时候我们已经走过了山林中的一条小溪,否则我们能否安全地穿过一个两米多的深潭还是个问题,没准还有一场洪水也未可知。遭遇雷雨和大雾后能见度急剧下降,而后山铺一线又是出了名地容易迷路。在没有任何导航装备和明确地图指引下,我们寻找着之前其他户外俱乐部留下的印记和标志,最终登上了一座……绝顶。
我清楚地记得那次罗老师是穿着一双沙滩凉鞋和跨栏背心开始爬山的,快到山顶的时候山风大作,没有吹散浓雾却只是降低了气温。罗老师换上了一件运动衣和运动鞋(不是登山鞋),我们面对着一块巨石,发现已经没有了前进的路,四周都是树和藤蔓,感觉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也许我们爬过那块巨石就可以和麻瓜的世界拜拜了。最终我们决定下撤,这个明智的选择挽救了两条因滑坠遇险的生命,也让濒临崩溃的罗老师有所期盼。
罗老师几乎是一路坐着搓着下山的,他体力上和精神上同时受到煎熬,这与我们出行前我承诺的腐败之旅差之千里。在没有任何登山经验和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这次出行直接把罗老师登山家的梦扼杀在了摇篮里,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原路下撤,终于回到了一处可以扎营的平地。那一夜,罗老师因为幽闭恐惧症失眠了。
——好了,忘掉这一切吧,罗老师,这次咱纯休闲,纯腐败,我保证。
——不信你问老王。
于是我们一行五人,乘坐早上7点开往怀柔的916。之前我定了后山铺琪琪农家院一个大炕的屋子,五个人住足够,100每晚。从车站下车包了个面包80块到达了后山铺。天气确实不好,风大概有四五级,天黄灿灿的。不过旅途顺利,到达农家院后,院子主人可以代买门票,25每人,女人们点了晚上的菜,计划很简单,整理一下就去爬山,回来吃饭睡觉。
农家院距离云蒙山森林公园大门两公里左右,农家院主人说可以免费送我们到门口,于是坐上面包车,哼着小曲儿到了景点。遥望远处群山叠起,植被葱郁,虽然空气中沙尘不少,但大家兴致高昂,开始爬山。这次爬山大家都理解成了纯休闲之旅,老王背了巨大的相机包,小萌穿了条拉风的低裆裤子,上面却穿了一件羽绒服,以耀眼夺目的姿态走完了全程(老王说,她一个人穿上了四季);罗老师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带了登山杖,穿了登山鞋,挎着相机缓步前行。但他们忘记了这云蒙山是一片险要的地界,爬到半山就开始狂风大作,头顶的云层迅速流过,终于在接近主峰的时候,天上飘下了细碎的雪花。
在飘下来的是雪还是冰雹还是雨夹雪的问题上我们有了分歧(罗老师高屋建瓴地说:这叫san【三声】雨字头下面一个散字,而后得意地笑。),尽管此时气温已经骤降,老王尽管对自己的秋裤感到非常满意,但刚爬过一段叫“铁脊背”的艰难路段后他已经感到很疲惫了,小萌的裤子影响了速度,但还坚持向上攀爬,走到最后面的是罗老师,他一定在想什么时候前面的人坚持不住了,绝顶下撤的时候,老子一回头就成功逆转为领队了。不过我们还是坚持向上爬着,张西开始闹恐高症,只敢面对着山体一侧走,但山上还是有不少游人,我们还看到几支勇于穿高跟鞋攀登的女子。经过一阵狂风,白花花的又飘下来一大片。终于我们看到一条很新的栈道,旁边有一个地图,一个箭头上四个大字“主峰方向”。
大家欢呼雀跃,吃了随身带的牛肉、巧克力,补充水分。这个时候小萌买的泡椒凤爪体现了巨大的价值,吃在嘴里马上就不冷了,解放军叔叔爬雪山时候喝辣椒水还是有道理的,要是有榨菜和肉丝那就更好啦。吃完了整理了一下行装,此时雪已经几乎停了,沿着栈道没走多远就到了主峰平台,拍了几张相片,忽然天空云层洞开,阳光倾泻而下,一时间,暖意盎然。我和老王相视一笑:“还等什么?来吧!”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
下山相对来说较无趣,大家都有些疲惫,想着山下的农家饭,一路上倒也无多少风景,实际上我们仅仅走了公园里1/3的路程,如果带着装备或者状态极佳,可以一直穿越到天仙瀑或者云蒙峡,不过云蒙山一带地势还是比较险恶,网上一些攻略都说容易迷路、崴脚甚至滑坠,雨天还可能遇到山洪。我们出来前就听说有两个70多岁的老爷子进山两天了还没下来,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后来看到新闻,说老哥俩有一个脚崴了,在山上扛了小四天,不过所幸被营救下山。老王说可以据此拍个恐怖片,我说就叫《老无所依之梦断云蒙》吧。)
终于下山了,此时天已沉了下来,山脚的风也有五六级了,我们等了二十分钟车才到。众人鱼贯入车,到了农家院终于可以慰劳一下自己的胃以及心灵了。要了大概五六个菜,烤虹鳟鱼必不可少,还有猪肉炖土豆、对于不吃肉的老王也有大盘的炒鸡蛋,和管饱的棒茬子粥。待主食上来,众人开始风卷残云。看到店里还有烤串两位女侠禁不住诱惑一口气点了15串,结果一尝味道大有问题。各位展开对口味和口感的合理联想,罗列了若干种肯能的原料,得出的结论就是一个:肯定不是羊肉。除此之外这一餐还算可口,并且都吃得很饱。吃完了以后回到农家院,众人翻滚上床,并排躺下,此时屋外山风大作。本来想一起玩牌但都困乏不堪,唯有躺在床上看电视是舒服的选择。这时要有一部诸如《将爱》或者《战国》之类的大烂片一起看那就有意思多了,可惜电视里只在播《非诚勿扰2》,一个“香山”一个“芒果”的烂名字让人一听就起腻,于是一赌气,睡了。
次日天明,大晴,晚起,吃了早点,收拾休整后回城,一路无话。记得我上一次游记里这样写道“坐上返回北京的 916 心情颇为复杂。虽然我们没有登顶云蒙山,但是我们却经历了难忘的艰苦旅程。对于我们,这次行程是难忘的并且是独有的。不仅让我们再次对山产生敬畏之感,更让我们对他产生亲近之心。这使我再次想到登山的意义。是的,有人说过因为山在那里,所以我要去征服它!”现在觉得以此句结尾也不为过,只需要把前面两句改为,虽然登顶,我们仍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旅程。或者就此打住,一段游记只有形式上的结尾,对于我们这么装逼的人来说,所谓旅行的意义——用存在主义的观点来看,不就是个虚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