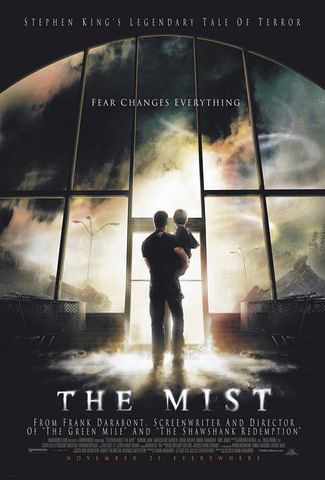整个春节我最期待见到的亲属就是我的表哥,但是他一直没有出现。我想他也许和我一样,对家庭聚会这种年度活动充满抵制的心理和严重的思想负担。
对于我表哥,每逢佳节都是亲戚朋友对他的终身大事做年审的时刻,他会被几乎所有人问同一个问题。在我的家族里,他享受着几乎是明星一样的待遇,我们都甘心情愿地做小报记者,做狗仔,打听每一个家族成员并把“合理化想象”发挥到极致。但直到今天,官方的消息是表哥的“对象”仍然没有被他“搞”上,我猜测其中必有很动人的故事,或者是感情纠葛,或者是心路历程。如果写下来,肯定能在家族中传唱几个世代。
诚然,作为家族中的明星和最具八卦价值的成员,表哥的每个消息都牵动着我们的心,而他也很有大腕儿风范的行事越来越低调。两次可能出场的家庭聚会他都没有出场,让大家揪了一年的心在新年达到了高潮。表哥最经典的一次相亲经历是这样的:一天上午,一个亲戚给他打过去一个电话,告诉他一个女孩的联系方式和基本情况,说:“你跟人家约约见个面吧。”下午的时候,亲戚接到了表哥的一个短信,上面只写着五个字:“她不适合我。”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快要感动地流下泪来。因为我知道,表哥很可能根本没有给那个女生打电话,但表哥以一个堂皇的理由让所有人都不至于难堪。表哥像一个真正的高手,简洁明了地终结了这份缘分,此等洒脱和冷静能让红娘和月老都自惭形秽。我想表哥肯定是胸怀大志,那些俗女都不在他的眼里,他的形象在我的想象力中无比壮大,如果真的由我写下关于我表哥的诗歌,我肯定安排一个女人来服侍这个不平凡的男人。
我这么替我表哥胡思乱想,而我的日子也没有多么的好过。前三年来我一直被“每逢佳节必思亲”的情怀所缠绕,而今天我可以“月圆人团圆”了,却倍感寂寥。
几天以来我奔波于城市的各个方向,参加作为传统的家庭聚会,本以为会很有趣的家庭聚会实际上让人感觉无聊且空洞。几年没见的亲戚们聚在一起也并不见得如何亲热,我仍然一如既往地被询问同样的问题。大人们因为孩子总有一些共同语言,而作为他们共同语言的孩子在一起又能干什么呢?我的几个兄弟之间其实也已多年未见,餐桌上说得最多的还是我的身高和我弟弟的食量。大概这两个话题还能说几十年,只要我大哥不出现,我还是家族聚餐时出席者中最高的人;我弟弟的脂肪肝控制的好些,多注意运动的话,他的食量还是一如既往的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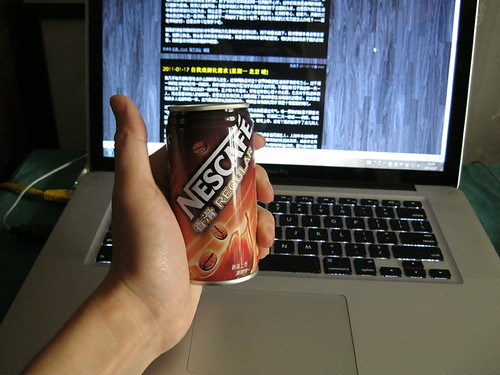

 读蒋勋老师所著的《舞动白蛇传》,提到杭州时有一句描写,说
读蒋勋老师所著的《舞动白蛇传》,提到杭州时有一句描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