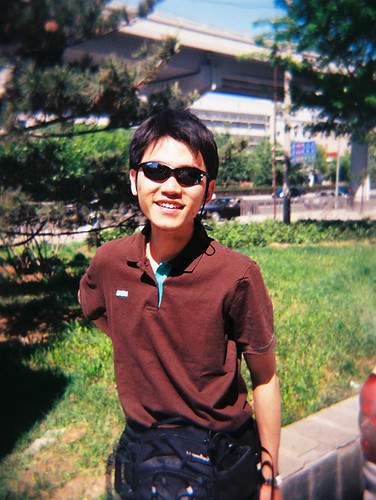Yes, it’s me!
不软110308 / 热情的沙漠
歌本来就是一首很火爆的歌,谁知道这个歌手的演绎更上一层楼,来自张蝶。因为热情,所以不软。
2011-03-07 阅读笔记 [星期二 北京 晴]
这两天再看蒋勋先生所著的《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延续了蒋勋老师一贯的温文尔雅的笔风,和他的讲座一样,深入浅出,不纠结与纯理论,而是从感性出发,讲理解,略带感情色彩。所以不难懂,正如封面上所写的一句话“九至九十九岁读者适合阅读。”

这本书列举了中国美术史上一些著名的画家的画作,全彩印刷,质量上乘。字数不多,排版讲究,阅读起来感觉很好并且是一本能很快读完的书。但这本书其实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读”,而在于看图并且识字。书中有很多作品都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代表作。蒋老师通过这些画作介绍了画家的风格和特点,只有看到画作,才能理解其在技法和意境上的高超绝妙。
有如下几点印象深刻处略记一二: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是中国绘画史上最被推崇的画家之一。他的《女史箴图》精妙细致的画风有个好听的名字“春蚕吐丝”,笔触细腻柔美;另一个大画家吴道子在画面精致程度上更高一筹,说他画的毛发都像从皮肤里钻出来一样,曰“毛根出肉”。不过画圣吴道子的笔触更加有力量感,画人物的服饰像有风吹过,被后人称为“吴带当风”。
讲到佛教绘画不能不提敦煌的壁画,其中一幅《鹿王本生图》的壁画看起来很眼熟,查了一下资料,原来以前看过的“九色鹿”的动画片就是“鹿王本生”的故事。
后又看到画马的名家韩斡,倒是记住了一个漂亮的马名,曰:照夜白。
2011-03-06 虹吸壶一点心得 [星期日 北京 晴]
最近买了虹吸式咖啡壶,算是我真正咖啡入门的第一把壶。之前家里有一把摩卡壶,是叔叔送我爸的,我用它煮过两次咖啡,很简单好用。唯一的缺点就是煮出来的咖啡还有不少渣子,我一开始以为是咖啡壶构造的问题,或者是咖啡粉磨得太细了,后来才明白是没有在底部放虑纸的缘故——这个失误显然很低级,但幸好是我自己悟出来而非他人指正了,让我少丢了些人。不过后来家里的摩卡壶电热底座坏了,只好弃在一旁。以后我打算给他配个支架用酒精灯来烧,岂不更酷? 于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挣扎和摸索,我终于在回国后四个月后入手了第一把咖啡壶,而这一次我直接把目光投向了咖啡壶中的Geek:虹吸式咖啡壶。
这是一把产自浙江金华的咖啡壶,售价仅85元,购买咖啡壶的时候同时购买了搅拌器和一个一分钟的计时沙漏。买最便宜的咖啡壶的原因也是第一次还是熟悉工具为目的,太好的壶怕玩坏了心疼。等熟练了再买一个日本原装的,或者直接升级,买一个比利时皇家咖啡壶。
经过几天的使用,发现虹吸壶不愧为体验咖啡文化的良品。对咖啡的享受不仅局限在品尝的那一刻,让咖啡这种在国人印象中的速溶饮品有了更全面丰富的体会。虹吸壶烹煮咖啡的过程能让人从视觉、嗅觉上获得多重享受。同时也强调火候、时间以及咖啡豆研磨的一些技巧。我家族里的亲戚很多人喝茶,家里的茶具一应俱全,来人就喝功夫茶。今天开始我也可以给他们显摆显摆,玩玩功夫咖啡了。
经过三次烹煮咖啡,有如下经验。
1、虽然这个壶提供了一个酒精灯,但是最好还是用瓦斯炉来煮咖啡。因为瓦斯炉可以控制火候,而酒精灯就只能靠移动酒精等来降温。操作起来着实不爽。
2、虹吸的好处是你可以对咖啡粉的用量有比较明确的了解。如果不用咖啡壶,恐怕会浪费很多。
3、目前看来,好的咖啡壶,两部分链接胶皮部分很重要,如果密封不好漏气的话,会很影响萃取效果。我第三次试验几乎算得上成功,已经看到上壶中明显的咖啡分层,但是因为漏气,让咖啡烹煮时间变短,没有完美。
4、虽然咖啡壶标配里没有,但是我发现一块吸水的湿布很重要,很有用。
5、咖啡滤布算是整个壶里清洗最麻烦的部分。但后来看了看网上的介绍。发现有的人洗滤布很简单,基本冲下水,用热水泡5分钟后放到一杯凉水中,放入冰箱。据说这样的咖啡布不会因为咖啡上附着的蛋白氧化而有异味,还能保留咖啡油脂在滤布上留下的香味。据说这个虹吸咖啡壶的派别就叫“滤布派”。瞅瞅,咖啡滤布都自成一派,玩虹吸壶的多Geek!
老王说:还得是胶片机。
2011-03-03 一本书和几个电影 [星期四 北京 晴]
芒克《瞧!这些人》
从罗老师书架上拿来一本书闲着翻,这本书的作者是当年朦胧诗的代表人之一。而这本书则是一本他的见闻录,记录了当年从白洋淀走出来的一批知识青年,他们在日后的中国文坛、诗坛、美术界和艺术圈都有着巨大的成就,很多人的大名今天已经是家喻户晓。但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就是讲述他们曾经的一些故事,通过芒克的眼看到,由他的嘴说出。
当年的白洋淀活跃着这样一批人:根子、芒克、多多、方含、宋海泉、白青、潘青萍、陶洛涌、戎雪兰、北岛、江河、严力、彭刚、史保嘉、郑义、甘铁生、林莽。除了他们书中还记录了诸如作者与黄燎原、王朔、陈凯歌这样的非诗人的交往记录。我觉得当年的诗坛是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群落,每个人都以诗歌的名义走到一起,却似乎谁也不能理解谁,很少能看出哪个诗人对同龄或者同时代的诗人的仰慕和钦佩,这帮人倒是见面就喝酒,喝多了就吵架,吵急了就动手,然后大骂一句:“XXX算个屁!他写的那也叫诗!”这个群落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斗士,都特立独行,只有像黄燎原这样涉世未深就被吸引的孩子才会表达出不能自已的欢喜赞叹。诗歌的世界魅力是不可言传的,我觉得很难说你能理解诗歌,但是你肯定能被诗歌所感动。
更有趣的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现代诗歌只能以几乎是畸形地状态发展成长着。这群诗人在当时几乎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代名词,芒克在刊印《今天》的时候也像是在做地下工作,他们的聚会也屡有警察跟梢。除了政治上的不自由,诗人也不像作家能成为一个职业,登大雅之堂,真正靠写诗来养活自己的估计没有几个。退一步讲,就连真正吃文字这碗饭的都少。就“以战养战”这一点来讲巴金同志绝对是靠笔吃饭的人的榜样,一个好战士。但诗人更多的不是靠打持久战,那样的激情的持续性是有限的,且对人有巨大的破坏性。诗歌不能满足人们引发的对自身的思考的平衡,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食指的精神病,海子的自杀以及顾城的悲剧都说明了这些。
书中说到顾城令我印象深刻,芒克第一次见到由姐姐带来的顾城的时候觉得他胆小怕事,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顾城的姐姐说他可没有你想象的那样胆小,在新西兰他一口气杀了100只鸡,这可是真真切切的。
对于诗人本身悲剧命运的思考其实在书中并不多见,很多文章都是写了芒克和他的朋友喝酒吃饭的故事。这些人虽然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插队,但他们依然是当年那批人中的佼佼者。我感到有趣的另一点是,这些人很多都有海外生活和学习的经历,在那样的年代有这种机会和际遇的,恐怕是更为难得的。《瞧!这些人》这本书我很快就读完了,但是其中的诗歌却没有细读,因为总有一种莫名的心理在作怪,我知道那些诗歌都饱含感情,害怕被吸入其中,难以自拔。
影片《127小时》

之前有一部片叫《荒野生存》”into the wild”,这部片子讲的也是一个到荒野去的故事,也是真人真事改编。只不过这一部电影多了一些面临绝境的体会,而少了荒野生存那种对于出行的意义本身的深刻思考。其实127小时给人的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压力,是个灾难片。在生存的最后一刻能否采取哪怕是最极端的措施,这样的假设本身就让人脊背发凉。而这部影片则真正拍出来了,让你看到,至少是血淋淋的,现实。影片最后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在遇难的第一天主人公就想到了折断手臂求生的方法,但到了最后一天才真正去做。影片中3分钟靠石头折断手臂的过程实际上现实中的阿伦·拉斯顿用了整整一个小时。
影片《暗夜列车》与《指环王》
 两个片其实一样,暗夜列车是列车版《指环王》;指环王是指环版《暗夜列车》。
两个片其实一样,暗夜列车是列车版《指环王》;指环王是指环版《暗夜列车》。
2010-02-28 月末记 [星期一 北京 晴]
 人物(左至右):小萌(的手),我,花轮,花轮带来的女孩,2毛,拍照者罗老师
人物(左至右):小萌(的手),我,花轮,花轮带来的女孩,2毛,拍照者罗老师
二月是双鱼座的二月,像某个歌者所唱:二月份的尾巴,三月份的前奏。时间亘古不变,但却日催人老。我参加了几个走入二十八九岁的人得生日聚会,体会着这些走入“二的尽头”的朋友们的信息与惆怅。这个情景总让我想起《Friends》里几个好友过生日时Joey哭丧着脸仰头大喊:“上帝啊,为什么这么对我!”而事实上,对于迷恋青春的人准备走进三十岁之前,心理何尝不都是这一番感叹呢?不多说了,只想起《刺秦》里的另一句台词: “喝酒,我要喝酒,拿酒来!”
花轮同学说喜欢吃日式料理,于是我们再次来到回转寿司。点了刺身、米团,面条炒饭,还有上好的烧酒。罗老师举着新入手的旁轴找着角度。我们坐到一起等待着2毛一行,结果2毛带着代表了他女人的冰激凌蛋糕姗姗来迟,一步三摇地走进餐厅,头显得越发的大。席间说了什么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大家都是艺术家,讨论什么都是在讨论艺术了。日本子的菜是有名的虚伪,光鲜亮丽但口味清淡。就连烧酒也没多大意思,开始我们怀疑是酒兑水了,后来想明白了,其实是水里兑了酒。2毛带来的冰激凌蛋糕还很不错,而且干冰造成的舞台效果给气氛增色不少,大家都很尽兴。
饭后2毛问:“你们是回方庄吗?”我们说:“是啊,我们打车走。你回哪儿?”他说:“那咱可以一起走,你们把我捎到37路车站。”“嗯?”我们好奇地问道,“你不是回西边么?怎么跟我们往东坐?不直接坐地铁?”“地铁不是2块吗”老王摇着大脑袋振振有词,“37块4毛钱,还有大座儿!反正我也没事儿,坐着车绕去呗!”
这就是2毛!这就是金牛座的2毛,我下一个要走到“2的尽头”的朋友!
我特意穿了皮夹克和皮靴,对于一个设计师,这样的装束简直是不能再正式了。鹏男看到我笑道:“你这身皮搂儿不错,装逼大大的有!”我腼腆地笑道:“人家真的是没衣服穿了。”鹏男给我们带了从泰国带来的礼物,两件大象的红色T-shirt。然后给我们讲述了他们在泰国5晚6日的旅行经历。不久人到齐了,还真多。除了我们和罗老师,还有他的同学,两个在泰国旅游时结识的朋友,还有一个韩国姑娘。该姑娘曾在03年在我们班交换留学,不幸赶上了非典,估计是没怎么好好学习,就忙着隔离了。后来回到了韩国,在做人参生意的家族企业里工作,也算是富二代了。我们行过了法式的贴面礼,以此告诉诸人:装逼,还是要身体力行的。
鹏男没有喝酒,但已然高了。把祝酒词说成了三句半,还带着大家唱歌。后来还和老婆一起唱了《真心爱人》并拥吻,场面一度很煽情。罗老师一路快门不断,拍了不少照片。夜色降临的时候大家作鸟兽散,鹏男一行还要赶下一场聚会,这里就按下不表了。
今天是二月的最后一天,罗老师说:“你们知道吗今天是大诗人李白的生日!”“呦,我操!不知道啊!”作为一个装逼积极分子我们还能怎么办呢?买蛋糕大家庆祝一下呗!于是直奔味多美,买了蛋糕,大家晚上一起喝着啤酒看奥斯卡。
20110222 入住方庄 [星期二 北京 多云]
今天买了一张桌子,白色的,花费226元。 首先我要感谢罗老师,他的慷慨让我们可以有缘住到一起。某年月日,我们入住方庄,开始一段同居生活。这几天忙的就是这个事儿。从决定到入住似乎经历了很长时间,但直到我们将所有行李卸下,布置好房间,打扫完毕,我才开始体会这一段生活的开始。我的手触摸着屋子的大门,想到John Lennon第一次见到小野洋子时得到的那个启示:呼吸。 我对北京南城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年轻时代的大半都是在崇文区经历。学生时代在这里度过,而今天又回来了,我想这就是缘分。用我妈妈喜欢的方式来说就是,不管你信不信,他让你来到了这里。我想是的,无论我多么的喜爱北京西北的群山,让我心底充实的还是站在山巅远望东南的时刻。 在罗老师家入住代表了我们新的生活的开始,我们以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于独立的渴望。自己买菜做饭,自己收拾屋子洗衣服。我们在巴黎独自生活的瘾还没有过够,也许再没有比这个更有趣的方式了。 入住方庄之后,罗公馆将以新的面貌示人。经过我两天的努力,终于把屋子80%的部分收拾了干净。擦地扫地自不必说,一个储物间内一块经年累月的污渍真是对人的一大考验。这块污渍让打扫卫生的我由衷的佩服起我自己来——这哪是在收拾屋子啊,这是在整理一段历史!这块污渍所含的丰富的内容足以见证历史上罗老师家一顿丰盛的美餐,经过消毒水和洗洁剂挥发出来的味道让我无比受用,就这样,我收拾,并感动着。
不硬110214 / 情儿
愿情人节有情儿,且皆成眷属。来自二手玫瑰,所以不硬。
不过我建议看此片mv,很有感觉,看了以后觉得歌更好听了。
2010-02-12 俯拍 [星期六 北京 晴]
未来的一段时间这里可能将是我窗外的风景。(我就是随便一拍)
以飞快的速度阅读着阿乙的《鸟看见我了》,这是阿乙的第二个中短篇小说集,我故意跳过其中的一个故事,现在发现这真是正确的做法。我在读最后一个故事,时不时向后翻看,只剩几页的故事就要接近尾声,但想到还有那个留给自己的故事就感到舒坦,好像一个想到还会有一个美梦等着他不希望到来的夜晚的孩子。